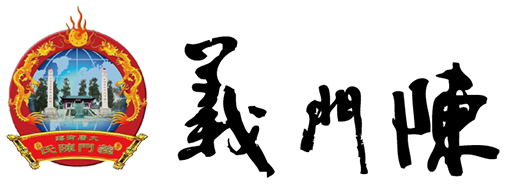口述/叶尚志 陈长璞 整理/季天琴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1979年,陈松年(左二)和陈长璞找到陈独秀的墓,此时只剩一堆黄土,碑已不知去向。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庆度过了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的求学生活。他自小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四岁的胞弟乔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陈独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陈独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怀宁乡下躲过,免遭毒手。
陈松年晚年回忆,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还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三个儿子。
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岁,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家的一妇女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让他们见见世面,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小兄弟俩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延年、乔年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陈独秀剖析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郑超麟回忆,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
昆仲双烈
陈乔年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
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
这些都是郑超麟记忆中陈延年、陈乔年的模样,“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
1927年,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一起被捕。
陈延年在狱中沉着冷静,说是这家主人雇的烧饭师傅,审讯他的特务看他黑黑的脸,穿着破衣,也信以为真。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江孟邹先生突然收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寄来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信,他拆开一看大惊失色。信上写道:“鄙人于6月26日被捕,现拘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烧饭司务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衣衫裤都破烂了,天气又热,请先生替我买一套衫裤来。谢谢!”
汪孟邹托胡适疏通,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便请吴稚晖帮忙,不料好心办成了坏事。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胡适都熟,又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帮助过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但陈独秀文笔不留情,骂过吴稚晖为老狗,又因延年、乔年兄弟在法国已公开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父子与吴政治上裂痕很深。
吴稚晖得悉陈延年被捕,惊喜若狂,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诬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的身份暴露。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龙华刑场站着被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次日,国民党的报纸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铲除共党巨憝》,大肆吹嘘“清党”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亲笔“贺函”。
陈松年晚年回忆,当时得到噩耗,全家如五雷轰顶,老者痛不欲生,只能由其妹陈玉莹、其弟陈松年前去处理后事,当时不仅不让收尸,而且连看都不让看。
第二年6月,二哥陈乔年被捕,年仅26岁,又在龙华遇害。又是陈玉莹、陈松年去处理后事,仍然不能看到遗体,其惨烈之情,难于言表。以至陈玉莹受到严重刺激,得了血崩症,一病不起,年仅28岁。
延年未婚,但乔年却与一位革命伴侣相恋之后结婚。在上海生有一女,在襁褓中其父乔年被捕遇害,其母只得隐姓埋名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互济会抚养,至今七十年,虽有些线索,但不知确讯。
没有人知道陈独秀得知儿子死讯时的情形。“托派”骨干濮清泉后来回忆,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监狱的大墙里后,陈独秀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松年一家
叶尚志还记得安庆东南角上陈松年的破旧蜗室,墙上挂着其父陈独秀四十多岁的相片,陈独秀留了一撮短须,目光炯炯。旁边挂着生母高晓岚女士的相片,一副大家闺秀气质。高晓岚1930年在安庆病逝,她抚养了亲生子女五人,除小女幼殇外,余皆成人。
大哥、二哥、姐姐惨死,家破人亡,处境艰辛险恶。在漫长的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只得韬光养晦,使他养成谦恭本分、与人无争的性格,与两位兄长性格迥然不同。
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
虽然日子十分艰难,但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在陈独秀人生最后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处境没有什么变化,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谈话间,毛泽东遂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傅说:“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
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最高领袖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有功底、见多识广的陈松年才被安排为市文史馆员,后为省文史馆员。1979年,正值拨乱反正之际,陈松年斗胆致信给安庆有关部门,要求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了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钱由官方出。重垒一座如百姓无异的坟头、再加立碑,共200元人民币。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在恢复政策后,陈松年子女陈长琦、陈长璞等作为“受教育子女”才得以返城。子陈长琦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长璞泼辣、开朗,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对家史非常钟情。
1981年,如先祖一样直率的陈长璞为陈独秀“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一位中央领导就坟墓一节做出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安庆市财政再拨款2万元,第二次修墓。这一次,墓身砌上水泥,但坟顶却未封,依旧黄土朝天,似寓意墓主人盖棺而论未定。碑也推倒重立,碑上只极简略地镌着安徽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题写的“陈独秀之墓”五个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眼瞅着为陈独秀平反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为何却又杳无音信。陈长璞却坚信冰雪终将消融。1998年,在李铁映、曾庆红的批示下,安庆的“陈独秀工程”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历代后人的推动下,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公理在一年年复苏。
同父异母的兄妹们
陈鹤年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他与三个哥哥延年、乔年、松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与姐姐陈子美为高君曼所生。在他10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就离开了父亲,来到了南京,从此他们与父亲分居了。
陈鹤年1913年出生,曾在北平等地求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在北大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一些后勤工作。但由于其父陈独秀等复杂原因,陈鹤年不为各方所容,后远走香港。陈鹤年在香港改称“陈哲民”,埋头度日。
反右开始后,陈鹤年的大女儿陈祯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最后却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就是因为她的祖父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父陈鹤年又在香港,有里通境外之嫌。
为了保护好几个孩子,无奈之下,许桂馨与在香港的丈夫陈鹤年宣布解除了婚约,以表示她与丈夫划清了界限。
即便如此,子女们还是未能走出阴影。二女儿陈祯荣在汇报思想时,天真地说了句“对祖父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年幼无知,到商店买毛主席纪念像章时认为价格太高,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又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1968年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鹤年的几个子女都陆续落实了政策。除了陈祯荣留在北京外,其他子女都去了香港。2000年,陈鹤年在香港走完了他帷幕深掩的余生,时年77岁。家人本着他一贯的低调,不予公告。
而陈独秀的次女子美,早年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经历不详。
上个世纪,陈子美落难成了牛鬼蛇神,走投无路之下,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儿子泅海偷渡香港。1970年,她身系五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到达香港。
在陈子美失踪后,世人都以为她已自尽,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
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刊发了该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对陈子美老人的专访。
原来,在成功抵达香港后,因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未等见其弟(陈鹤年),陈子美便又经千辛万苦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岂料1991年她因病住院回家后,却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拿走,从此只好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因积欠房租一万四千美元而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欠款,88岁的她就只能流落街头。老人只筹得两千美元,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当地报纸披露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陷入困境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已应其本人要求提请法院延期审理此案,并资助了五千美元,但仍欠七千美元。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闻此讯后,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九千美元汇给了陈子美老人。
一个月后,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派出两位领事携鲜花前往老人的住处探望,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陈子美遂于次日在住处召见记者,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长璞去美国探亲时曾见过陈子美,她评价这位姑姑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2月25日,陈子美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此间无任何亲人来看望她。4月14日下午4时,陈子美客死纽约。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少有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